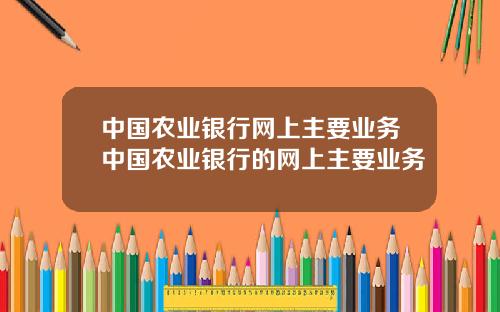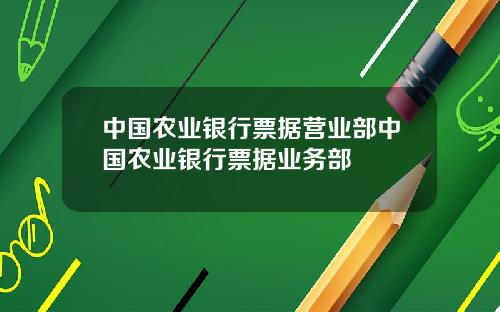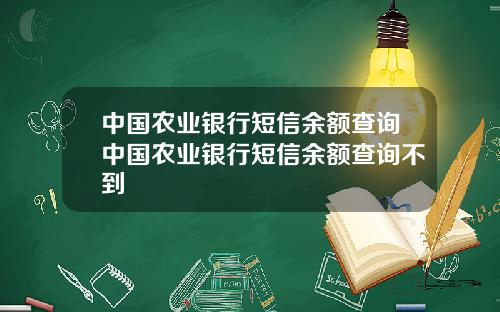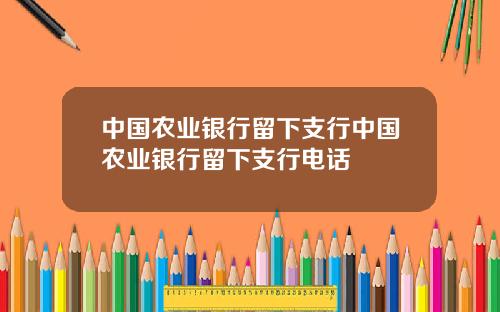文章目录:
1、【云南网专访】段四兴:剑川木雕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2、寺院掠影|云南嵩明法界寺,我们的法界寺3、美丽中国丨印象大理
【云南网专访】段四兴:剑川木雕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
前言:剑川木雕在云南人的眼里,不仅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件件艺术品。在云南的很多地区随处可见剑川木雕作品,建筑物上、门窗、家具、摆件,雕梁画栋、精雕细琢,一凿一锤间,美轮美奂的缠枝花卉,栩栩如生的花鸟虫鱼,活灵活现的飞禽走兽。这些正是代表着云南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近日,记者在云南网演播间“云游非遗故事会”系列专场直播现场,对话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剑川木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段四兴。
人物名片:
段四兴
正高级工艺美术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剑川木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负责人、大理传统工艺工作站(剑川基地)负责人。云岭首席技师、全国劳务品牌形象“剑川木雕工匠”代言人;中国民族工艺美术大师、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乡村文化和旅游带头人、国家乡村工匠名师、云南省第四届百名拔尖农村乡土人才、云南省乡村工匠名师。
剑川是滇西的一个小县城,整个县人口有16万左右,从事木器木雕的人员就有2万多人,是当地一项惠民产业。段四兴就出生在这个小县城。
因为祖祖辈辈以木雕为营生,从小耳濡目染的他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剑川县职业高级中学学习绘画和木雕设计,开始接触线描和素描,后面是图案课和木雕基础课,毕业后进了县里的民族木器厂。
潜心创作的段四兴 供图
制作木雕是一个极其繁复的过程。每年中秋节过后到次年的清明节之前采集油性较好的冬木,然后立意、绘图,随后下料,接着把图纸贴到板材上,就开始打粗胚、打细胚、修光,最后就组装跟上漆。这些过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因为剑川木雕属于镂空深浮雕,每凿每锤,层层雕琢;均需屏气凝神,才能呈现出生动立体的作品。“天赋可能要有一点,但最主要的还是执着。”段四兴说。
剑川木雕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剑川世代创作木雕的家庭不在少数。就像段四兴说的:“从小在木雕世家长大,可以说剑川木雕已经融入了我的血脉。”1979年,段四兴的父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木雕的装饰工程。40年后,也就是2019年,段四兴团队又承接了人民大会堂云南厅的木雕装修工程任务。在云南民族博物馆,还有一幅长97.6米、高1.8米的大型木雕壁画《张胜温画卷》,昆明震庄宾馆水榭里面的木雕装饰工程均出自段四兴团队之手。
段四兴和他的木雕作品 供图
40年不断磨砺不断精进,勤学苦练使他的技艺日臻完美。2018年5月,段四兴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剑川木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更好地传承剑川木雕,段四兴和他的团队在迪庆州、怒江州等多地长期举办木雕技艺培训班,还招收了独龙族、傈僳族、怒族、藏族等不同民族的学员。培训学员可以通过职业技能鉴定,取得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为了更好地推广,南博会、文博会、旅博会、国际非遗节、非遗博览会等国内重大的展会上都有剑川木雕的身影,并走出国门参加了瑞士、德国的相关非遗展示活动。
伏案工作,难免枯燥,为了让自己保持对木雕的热爱,为了保持技艺的熟练度和创作的新鲜感,不让自己“手生”,无论多忙,如今两鬓斑白的段四兴也没有放下手中的凿和锤,他几乎每天都会抽空创作、雕刻,并保证每年出品1-2件作品。
“教学过程中,我能够将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同时也能从年轻一代的视角中获得新的启发。这种互动有助于我保持思维的活跃和创新的能力。”段四兴说,他会定期创作、持续学习,不停阅读、参观展览,与其他艺术家交流,不断吸收新的艺术理念和技术,丰富自己的创作灵感,传承好这门国家级传统美术非遗项目。
云南网记者 郭凯 秦黛玥
寺院掠影|云南嵩明法界寺,我们的法界寺
云南嵩明法界寺位于嵩阳镇山脚办事处的灵云山东麓,创建年代不详,有文字记载的是在明代成化年间已作维修,至明末崇祯时,已是殿宇层叠,庵、坛、观、楼林立,佛、道两教合流的大型建筑组群,丛林位居嵩明八大寺之首。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对法界寺曾与记述。经历代重修、扩建,法界寺成为规模宏大的佛、道寺院建筑群。
1989年,嵩阳镇群众自发在性海庵原址建砖木结构平房6间,内塑观音、文殊、普贤等佛像;另建房4间,作办公、住宅使用。
1997年,嵩阳镇政府及所属山脚办事处(村民委员会)决定利用灵云山自然景观和法界寺的历史影响,用15年时间分期开发建设占地2平方公里融观光、旅游、度假和佛教文化发扬为一体的灵云山法界寺森林公园。一期工程包括重建法界寺大雄宝殿,完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
于当年11月15日奠基兴工,至1999年1月18日竣工。按原址原貌重建的大雄宝殿,为五间重檐歇山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长21.4米,宽18米,高14.6米,琉璃瓦屋面,剑川木雕门窗,大理石平台围栏,霓虹灯屋檐装饰,殿名匾额为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墨宝内塑如来、药师、阿弥陀佛像及五罗汉群像;在大殿左右建二层楼厢房19间,供公园管理人员工作及僧尼居住;整修了大殿左右两侧的白龙潭,再现"双泉泻碧"景观;沿专用公路建成山门三道,气势宏伟,颇具观赏性;在二天门西侧建露天舞台,供游客集会和开展文艺活动使用。
法界寺所处的灵云山,素有“半朵莲花” 之誉,山上寒松傲雪,两侧双泉泻碧。法界寺不但建筑林立、碑碣众多,而且佛事兴盛,最盛时僧尼道士达数百人之多。
然而,由于历代兵燹和缺少维修等原因,法界寺被毁,只剩下几块残碑可寻觅的遗址。
法界寺从明成化壬辰8年(1472)至清道光,几经维修或重建,至民国中期,已毁败殆尽,仅存一殿。
现在的观音殿,系1989年于性海庵原址重建,之后,先后建成大雄宝殿、天王殿等建筑,全为钢混结构的仿古建筑。
民国时期至上世纪60年代,法界寺被毁怠尽。1989年,香客集资重建观音殿。
1997年开发法界寺森林公园时,重建大雄宝殿及两厢房,后又修建了天王殿、财神殿、文昌宫、龙王殿等殿宇,均为钢混结构仿古建筑。
现存有明代立的《重修法界寺设龙华会碑记》《丛林碑记》及清代道光年间立的《重修真觉寺碑记》。
1999年7月5日,嵩明县人民政府公布法界寺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1638年9月28日,徐霞客来到嵩明考察盘龙江水系源头,在等待嵩明县衙门回话途中,出西门游览法界寺,并写下了至今已经378年的法界寺游记。徐霞客虽然到嵩明法界寺是为找南京僧人,但是,他留下的足迹和文章却是难得的,徐霞客在1638年9月28日来到法界寺法界寺写下的374年前法界寺的面貌如下:
余从间道北向法界寺待之。法界寺者,在城西北五里,亦弥雄山东出之支,突为崇峰者也。路当从西门出,余时载岗逸眬,下度一竹坞。
二里而北上山,蹑坡盘级而上,二里,迤一东下之脊,见北坞有山一支,自顶下垂,而殿宇重叠,直自峰顶与峰具下。路有中盘坳中者,有直蹑峰顶者,余乃竞蹑其顶,一里及之。
西望峰后,下有重壑,壑西北有遥巘最高,如负庡房契领,拥列回环,瞻之甚近,余初以为嵩明之冠,而不知其梁王之东面也。
转而东,峰头有元帝殿冠其顶,门东向,仍道宫也,余人叩毕,问所谓南京僧者,仍不得也。先是从城中寺观霓之不得,有谓在法界者,故余复讉途至,而岂意终莫可踪迹乎。由殿前东向下,历级甚峻。半里得玉虚殿,亦东向,仍道宫也,两旁危箐回合,其景甚幽。又下半里,有一庵悬岗之中,深竹菴门,重泉夹谷,又下,始为法界正殿。
由此可见,在近300多年的时间里,法界寺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优雅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如今能够恢复法界寺已经很不容易了,300多年以来,沧桑巨变,嵩明县一些文物古迹已经荡然无存,今天,能够看到徐霞客游法界寺的文章,非常可喜可贵。
徐霞客千里迢迢,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难险阻,不为个人得失,来到云南嵩明县考察盘龙江源头的历史记忆,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
兰茂(1397-1476),字廷秀,号止庵,又号玄壶子、和光道人。明代医药学家、音韵学家、诗人。兰茂生性聪颖,勤奋好学,少通经史,旁及诸子百家,终身隐居杨林乡里,采药行医,潜心著述,设馆授徒,人称“小圣”。著有《滇南本草》《医门览要》《声律发蒙》《韵略易通》《玄壶集》《经史余论》《止庵吟稿》《安边策条》《性天风月通玄记》《山堂杂稿》《续西游记》等传世之作。
文章来源:嵩明生活网
美丽中国丨印象大理
沙溪镇玉津桥,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过江桥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一
在喜洲古镇采风时,我趁大家观看展览时独自走到镇里的街上游览。游客虽不多,但胡同和街角的摊位依然有人光顾,我就对着那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小吃、竹编制品、扎染服饰、银首饰使劲儿看。
走到一家卖下关沱茶的门店前时,老板娘招呼我进去坐,我礼貌地摆摆手,她就走出门来和我聊天。
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老板娘身边站着的一位大姐很兴奋地说,她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工作过,我问她孩子们为什么没有继续留在北京发展,她说都回老家来了。老家现在也有很多项目可以做,家里老人还能帮助他们带带孩子。
这里,每家门店的名字都很独特:茶缘,喜传,槲寄生……
静静的街面上,我抓拍到一张年轻的妈妈喂孩子吃饭的照片。她是扎染店的老板,门面上挂着五颜六色的桌布。她看我盯着黄色和褐色相间的那块桌布,就说,便宜卖给您,80元。其实我无意买桌布,而是诧异扎染不都是蓝白相间居多吗,怎么还有别的色彩呢?我真的是在此长了见识。
我几次停留在那个挂着“漫漫-慢慢-古法手工品”的门前,可惜人家没有开门。我在想,门里面的手工品都有哪些种类呢?右首,是一家白族风格的庭院,门楣上书有“清白传家”四个字,门框上有一块牌匾,上写“蘭尚居”,再右首,是尹氏宗祠,更显年代痕迹。
最有看点的是那家“熙渡茶画会”,门面就是一扇开着的窗口,窗帘半挂着,隐约看得见里面的瓶瓶罐罐。窗台下,摆着两把掉了漆的蓝色圈椅,那圈椅没有腿,摆放在长条的陈年木板上,远远看去,沧桑感叠加,别有一番意趣。
街上也有现代气息的门面,简易的白色铁艺桌椅配上老旧的门窗和花草,营造出别样的氛围,静待游客前来喝茶、喝咖啡、聊天。恰好,这个门店就在喜洲农耕文化艺术馆庭院里。
有那么一刻,一行人闲散地坐在庭院里,望着院子里那两棵百年古树,琢磨着、品味着当年喜洲选址时所遵循的“不城不市不区”的理念。
喜洲呈现的田地有美感,整齐划一的阡陌田垄、精心耕作的田园景观,尽管连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都说土地是乡下人的命根,但喜洲掌握良田沃土的士绅们却将生活的底色铺在了传统农耕的习惯上,铺在了善耕善种的农民心上。
喜洲镇在云南大理是一个很特别的白族小镇,以喜为名,以洲而域。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在南诏、大理国年代,这里是一座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大理县志稿》中有记载:“至于商务思想,惟喜洲一地人物为最优胜之资格。”
民国时期的喜洲商帮将喜洲的经商传统发展到极致,出现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等24个有代表性的商业集团。有人说,他们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滇西GDP制造者。
此话不虚。当我们参观了那个代表着喜洲农耕气息的展览馆后,对喜洲重商亲农的习俗更有感触。
“土地是一个大写的创造者。”这句话就写在进门处。
曾几何时,那些拥抱过世界的喜洲商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家乡有独特的风景和无可复制的田园生活做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啊。
可以想象,喜洲几代人情感绵长的乡愁牵动了多少喜洲游子难忘的寻梦旅程。但他们要落叶归根,在属于喜洲的田地里休养生息。
可贵的是,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走出去,再回来,喜洲人早就具备开放的心态,我们眼前的魅力家园就展示出了他们的胸怀、雄心和壮志。
二
“哎,那个剑川来的小伙子。”这是电影《五朵金花》里的一句台词。自此,我就知道了云南剑川这个地方。据说金庸所著的《天龙八部》,开端和结局也都是从剑川起笔落笔。
千百年来,茶马古道从剑川穿过,多少途经此处的马帮喝过剑川的米酒,听过剑川的迎客调。
代代相传的木雕工艺让多少剑川工匠袒露赤诚心愿。我在一家小小的木雕门店里给父亲买了一只烟斗。店主说,这就是个念想。其实,我就是冲着这句话买的,并理解了那“念想”蕴藏的深层含义。
了解剑川的最佳方式,就是参观这里的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馆。
街心广场的地面上,有用心设计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地图。路线走向,途经地名,东西南北相连接的地方……这条被誉为“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的商道,曾经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南方丝绸之路分馆,再现了茶马古道千年风貌。
千年,从古代到现代。一条南方丝绸之路跨越万里长途,连接世界,商通四海。今天大家都在说“丝路精神”,再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去感知和解读时,会更清晰、更全面。
“丝路精神,根植于历史,面向未来;源于中国,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其内核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从一条街,看一条走向世界的通道。遥想500多年前,是谁驻足剑川,让远来的风华呼啸而来?一馆尽览百年剑川沧桑。
站在剑川,转换视角,找寻专属剑川的表达方式。
在世人眼里,那些沸腾着生活气息、融合个人奋斗与家国情怀的时代叙事,持续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而将丝绸之路地图篆刻在广场地面的背后,有多少人走在路上,有多少货物流通世界各地,有多少人摆脱局限将目光转向国际市场,一种“走出去”的勇气满足了多少人出行的想象?
在南方丝绸之路分馆,我的目光所及之处,由远而近,看到了商人们用脚印写成的诗行。一排排诗行,竟是那样气宇轩昂。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靠近或走近时,才能沉下心来重新认知一段历史。人们常说穿越千年时光,怎么穿越?
就在由数字光影打造的“时光隧道”和“八荒纵横贯古今”的沉浸式穹顶空间长廊上,我们真的穿越了——
丝路四季,丰盛的物产,各地的风貌,热闹的集市,行走的驼队,美丽的江河、雪山和平原绿洲……长长的路上,无尽的风雨,无尽的收获。从探索到发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地区和人们就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剑川周边,湖水荡漾,水鸟飞翔;剑川古城,书香浸润,文脉相传;剑川百姓,生活富裕,诗意栖居……对我们所有的梦想进行归类分析时,尽情寻找规律,没有任何限制地进行思考,打开思路。
在剑川沙溪镇,我记下石龙村喜林苑这个地名的时候,已是夕阳西下。山风起了,略感凉意。
体验白族文化,体验石龙村特有的文化景观、生态景观、村落景观和田园景观,一行人在纯朴的田野空间里和村民们一起歌舞。村里的演出队都是由本土优秀歌手组成的,石龙霸王鞭,白族调,一招一式,一唱一喊,都是原生态的味道。
据当地文旅局的同志介绍,这个村里的村民就是当年舞蹈家杨丽萍导演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的主要演员。彝、藏、佤、哈尼等10多个民族原始、粗犷、充满绚丽色彩的生活,在歌舞中生动地展示了出来。
我曾经采访过杨丽萍,记得她说她要用古朴的肢体语言来表现民族自己的东西,将那些原汁原味的舞蹈、被遗忘的舞蹈语言还原,寻觅与生俱来的那种冲动和欢歌。
舞台上的道具、牛头、玛尼石、转经筒全是真的。70%的演员都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只是我当时不知道他们大多来自石龙村。
茶马古道上的沙溪,给了横断山脉地区一抹亮色。
马帮的铃声在山间回响时,沙溪周遭的盐商、货商们的心仿佛都长了翅膀。那些驮在马背上的茶叶、毛皮、布匹、药材,还有诸多日用品,都寄托着他们商贸交易的一个又一个新的开始。那些大米、食盐、香油和乳制品,则在晨曦中给热闹的集市增添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听风,看雨,本就平常的生活,在沙溪却总有翻检记忆的诗意。
三
车子沿着乡间的路缓缓驶入了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
被称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东莲花村,也是“马背上驮出来的村庄”。我们在这里的马家大院看到了马帮文化的过往。
茶马古道上的“山地之舟”,这是人们对马帮的比喻。古道茶香,巍山产好茶,早在一千多年前,巍山境内就开始种茶了。普洱茶香飘四溢,驱走了赶马人一身寒气,也温润了“茶马互市”的人文精神。
马帮有群、伙、帮的分别。九匹骡马为一群,三群为一伙,所有马加在一起就是一队大马帮。
“喜洲帮”“鹤庆帮”以及巍山的“回民帮”,就是传说中茶马古道上著名的云南大马帮。
在马家大院落座,休息片刻,静观院内最高的角楼,看着那一扇扇格子窗散发着岁月的气息。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怎么想象,也还原不出当年以马家兄弟为首的七支大马帮、几百匹马远走东南亚的豪情,但这建筑精巧的院落能够见证财富的积累和蕴藏在民居里的旧梦。
巍山古城的傍晚蕴藏着属于她的故事。
沿着古城后所街边走边看,吸引我的总是门两侧的对联。诸如“书庭桂院溶溶月,深巷睦邻暖暖风”“诗书礼仪流年立世,善德敦仁柏院沉香”。最让人揣度的,是一个院子牌匾上写着“理想国”三个字,底下有一行小字:我们贩卖的是生活方式。
想着刚刚路过的南诏博物馆庭院前的对联“珍藏瑰宝集撷精华佐证边陲文化,浓缩时空恢弘物理大观南诏风情”,我顿时被折服了。在巍山古城,竟然蕴含着如此深厚广博的文化理念。
一家一户所尊崇的这种文化理念直接带动着一种文化的传承。
以往,每到一个地方常常是步履匆匆,可在巍山古城却静心从容,其实,早已被这里随处可见的文字所征服。
这里每条街道都很整洁,且没有刻意装扮的成分。顺着临街的泥土斑驳的墙面,那用石块堆砌的墙基前面,摆放着朽木搭建的花架,那朽木透着年轮的条纹,留有之前被当做车轴或门框的形状。古朴的花盆里种着兰花,花架上下各摆一盆,仿佛立刻让花架增添了身价。
正是因为注重文化,才有了这般的街景。
在文华书院对面,是一个小公园。靠马路的一角种植着一棵清香木老桩头,近看好像是三棵老树相拥而成的样子,少说也得有百余年树龄了。
当地文联一位教师出身、后在文教局工作过的同志是我们的导游。每到一处,听着他熟练且幽默的介绍,我们想不记住都难。
特别是当我们走过一个叫“蕙兰苑”的门店时,他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这名字是店主委托他起的。
“想问我为什么这么热心起名是吧?”他说,大多时候是他主动而为。对巍山历史和文化有研究的他,当然希望自己的故乡依然保有文化气息。于他而言,这是无法推卸的责任。因为热爱,所以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我反复举起手机拍摄,每一处新发现,都让我体会到一种壮美情怀。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感觉处于巍山的院落、山水、农田,甚至陈年旧物都熠熠生辉。
每个庭院的看点、历史和当年的文化氛围,都在告诉我看什么,怎么看,沉浸于百年前的中国庭院中,我毫不遮掩、毫不吝惜、毫不回避对美好生活的赞颂。
巍山的关键词很多,像我一样等着聆听“喜欢巍山某某事物”这类话的人也很多。在汇聚着居民与自然、连通着天地和美的巍山,果真能在屋檐下的风铃声中体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境界。
巍山温润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