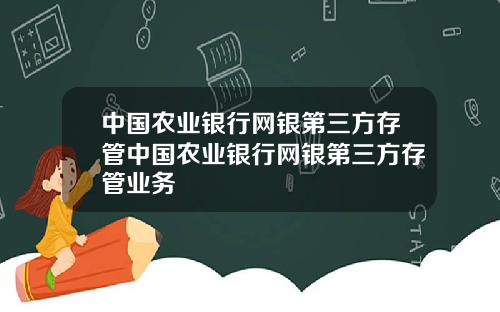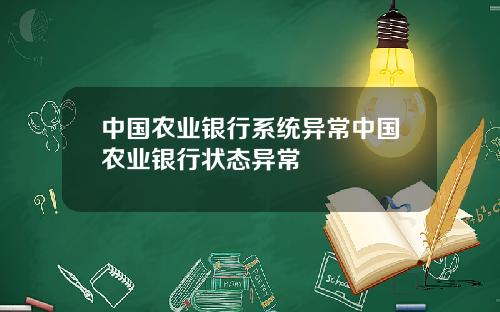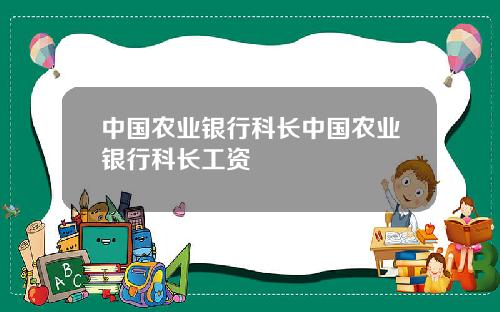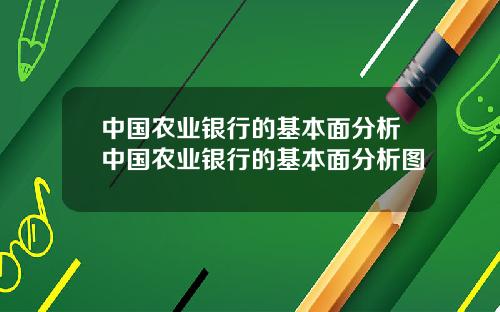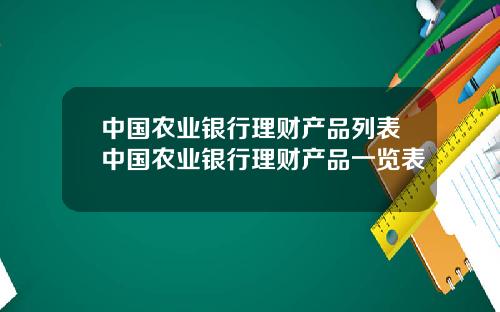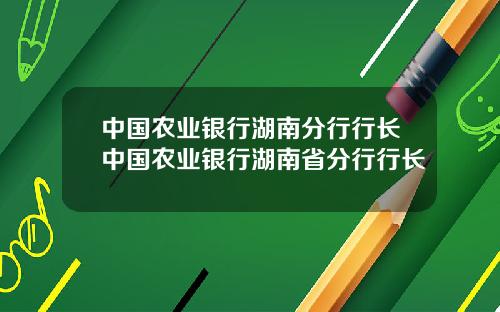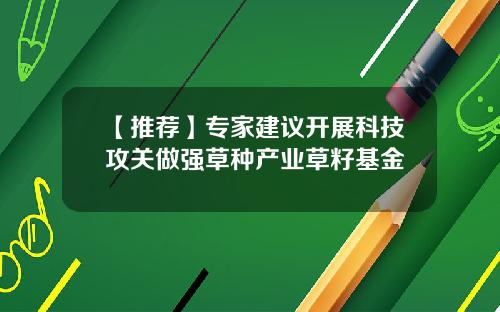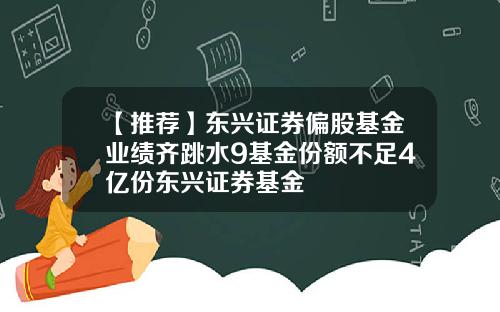农历新年,在孩童“噼啪”的鞭炮声和亲情团聚的意念支配下,分外催人,心急意且,思绪早已飞旋在童年的乡村街巷中。大年初二,欲回老家的我们,决定前往距老家不远的妻子姨姨家,看望年已八十有四的老人家。车辆驶离县城,顺洮河而下不远,过洮河在谷间水泥路上向大山方向前行,翻越一座山巅后下山再次与洮河相遇,过洮河溯流而上不远,老树掩映下的村庄出现在眼前,熟悉的老村映入眼帘,到达姨姨家村庄。停下车辆后,拐过一个岔路后,我们穿过一条熟悉、悠长又洁净的街巷,街巷的尽头,就是姨姨家。三阶水泥台上,红瓦覆顶、红砖门墙、灰黄色的木门,在阳光下,宁静、古香,门被木门栓从里面被顶住,我们判定姨姨一定在家,轻扣门环后不见动静,妻子打通了姨姨电话,我们得以进入姨姨家。
时光仿佛凝固在姨姨家洁净、整洁的院落中,花园砖砌栏杆笔直利落、上房房檐台阶上两把躺椅在阳光下显得分外白净,沙发上布面也是洗成耀眼的白、后院通往厕所的小径及厕所地面上一尘不染,靠墙处,是堆积的筛过的草木灰,草木灰也是经过精心打理过的,坡度、地面相交处是整齐的直线。两侧园地不见枯枝落叶,唯有发黄的土地和未消融的积雪,正房、厢房的四扇木质花格窗依旧随老屋伫立,默默陪伴着年迈的姨姨,增添了我童年无尽的回忆,时光仿佛在院落中凝固。
四扇花格窗历经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九十年代经济大发展、二十一世纪乡村振兴直至进入新时代,在表哥、表姐们无数次动员意欲改造为玻璃窗时,改造工程均被当时在世的姨父在规划阶段胎死腹中,姨父过世后,老屋的所有成为姨姨对姨父怀念的寄托,不得动之丝毫,花格窗就这样得以随老屋永存。
姨姨虽然是八十多岁的高寿老人,但身体硬朗,耳聪目明,见到我们,高兴的像个孩童,问这说那,有说不完的话题,指挥着表哥给我们倒茶倒水,端出糕点、油馍。姨父已经作古四年,姨姨给我们述说着姨父曾经的过往,言语中,满是对姨父一路陪伴的念想、羡慕、尊崇。姨姨虽然年迈,但记忆很好,把亲人们都问个遍,上至我母亲、下至侄子的孩童,都能说出名字、记得性格品性。姨姨虽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对小辈的关心深深烙刻在血液中,有说不完的心里话,一遍又一遍的劝我们吃这个吃那个,被长辈关心虽然是幸福,但望着年迈的姨姨,听她讲姨父辛苦、辛劳的过往,泪水不由自主的在眼眶中打转,我生怕让姨姨看见,勾起姨姨的伤感,赶紧找个借口转到后院,让阳光平复心情、用室外的冷空气驱散眼眶中不争气的泪水。
我远在瓜州的表哥是姨姨的侄子,我打通表哥的微信视频,看到娘家的侄子,姨姨微笑着和表哥说话,家中子侄更是记忆清晰,学习情况、身体健康状况一一问到,对娘家家族兴旺的期盼、祝福深埋在言语中,频频嘱托表哥少喝酒、把身体保护好。
亲情笼罩的时光分外短促,夕阳已经西下,我们在姨姨的挽留声中,踏上了回老家的路途,车辆驶入公路,回望姨姨,依旧伫立在大柳树下遥遥向我们挥手,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
作者简介
杜胜林,卓尼县公安局政工科三级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