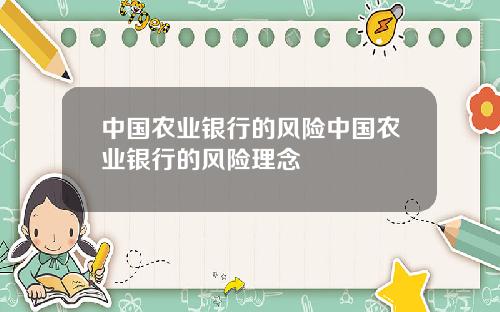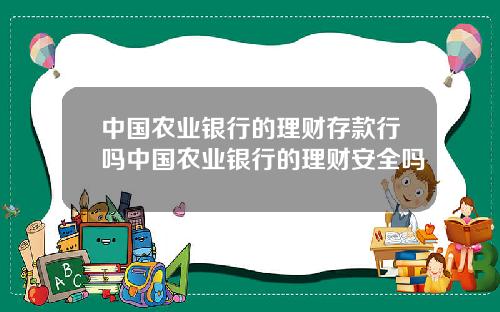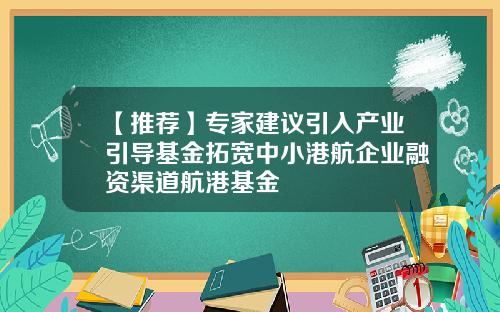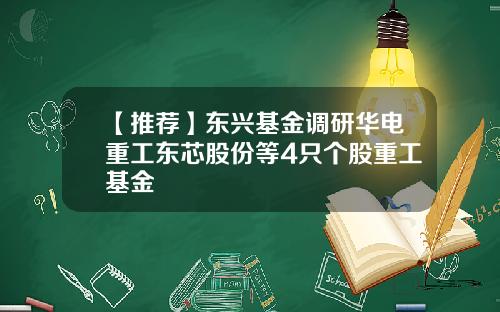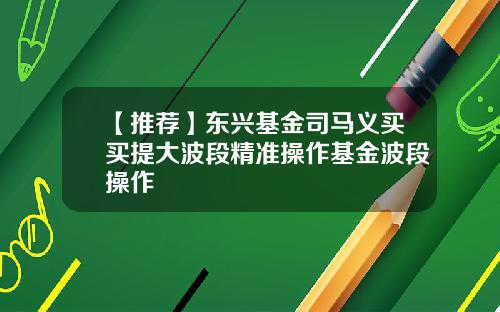换房记
严淑英
回想第一次走进西关街汪家弄的情景,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因为小哥在外地无法参加中考,全家从乐平的一个小煤矿坐上长途汽车,回到了广丰。父亲并不是矿工,是去投奔姑姑的。我们住在姑姑家的菜园子里,姑父给搭了一间小平房,一家六口人的嘴和四个孩子的书包全靠父亲摆水果摊养活。小时候最羡慕姑姑家的电视机、热水器还有好看的房间。听说要搬家,当时唯一的愿望,就是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
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拎东西,是怎么走进的汪家弄,那条长长的、窄窄的小巷子。这一条长巷真好啊,隔绝了街面上的喧闹,像陶渊明进入桃花源时走过的那一段路,走到底,“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开阔便出现在眼前。
继续往里走,是我们的厅堂,汪家弄也叫堂门家里,堂门倒是没看到,据说原来有,后来新华书店扩建,把堂门拆了。不然我进堂门家里的那天,就应该是从正儿八经的堂门里进来了。小小的堂门家里一共住着七户人家,母亲说这些原来都是太爷爷的,连同后面的几间店面,开着广丰名号响当当的南货店。
太爷爷的故事就像电视剧里一样传奇。太爷爷小时候也是贫苦人家出身,从小被送到县城学徒,后来因勤奋努力被老板看中招为女婿,从此在县城立住了脚,开枝散叶。可以想象得出,这里曾经是何等的辉煌。厅堂依然完好,左右两边各一个房间,右边那间就是汪家七号。
然而,在小学五年级的我眼中所见,只有破败、老旧和昏暗。我确实被分到了一个小房间,小到几乎只放得下一张床,没有窗,没有门,用一块帘子表示了禁止入内的意思。房顶上总是掉灰,墙壁粗糙到贴不上墙纸,晚上总有老鼠来跟我打招呼。尽管如此,那一年的我还是因为分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欢喜不已。
电在我们搬回来没多久之后就全通上了,自来水过了几年也用上了,再过了些年,厕所,热水器,洗衣机也逐渐安排上了。而我的房间,也不断升级。从那个黑漆漆的小储藏间变成有大窗户带厕所的房间,是小哥考上大学去外地念书的那一年。这个房间,我住了三年,从高一到高三,后来大伯告诉我们那个房间在他们小的时候是吃饭的厢房。厢房原来只在一堵泥墙上有一个方形的洞算作窗户,后来风吹雨打索性推倒重砌了一面砖墙,顺带做了个厕所,结束了我们一家十分钟路程上厕所的困扰。墙上窗变成了有杆有门有栓的玻璃窗。当然,住着全家唯一有厕所的房间还是有烦恼的,比如需要半夜起来给需要上厕所的人开门,一大早被爸妈的敲门声叫醒……
2016年学校毕业,选择了考回小县城当老师,也终于尘埃落定,回到了汪家七号。当我再次踏进那条深而长的巷子,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看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小巷,邻居们便惊喜地冲着汪家七号里喊“你们的哈妹回来了!”看着母亲从老屋里走出来,脸上带着笑,回神:我是属于这里的。
这次,我的房间又换了,告别了公卫的尴尬,换到了全家条件最好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既有楼板又有窗户,私密性好。工作半年之后发了第一笔工资,给家里添置了全自动洗衣机,给房间添了柜子、衣帽架、风扇,还买了桌布、相框,卧室更像样了。
这么多年过去,我也从那个一脸嫌弃的小姑娘变成了钟情于老房子的大姑娘。出嫁的时候,买了一堆中式复古的东西来装饰这个房间,我花的心思赶上了男方的新房。这是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心地让老房子彰显出它的魅力。大红的绒布喜字,贴在木门、木窗和雪白的墙壁上,精致的灯笼挂在楼板上,喜庆的绒布拉花挂在花床上,那一天的汪家七号是喜庆的、精神的、明媚的。
如今,棚改的春风吹遍了广丰,汪家七号也乘风飞翔,被改造成一个小广场,父亲母亲也将分得新房,这是母亲盼望了一辈子的事。2017年,大哥乔迁,我们一家人从各地赶去中山,母亲即使晕车,也坚持了十几个小时。她的心里该有多高兴,这是我们这一家子里第一回办这样的喜事。2018年,小哥在杭州结婚加进新房,母亲提前就去住了一阵,西湖也顺便玩了一圈,过了几天神仙日子。2019年,我在广丰结婚,婚后也买了一套房,虽然没在大城市,不过父母也很替我高兴。
父母亲原本只有一间房一个家,现在他们二老在中山、在杭州、在广丰各有一个家。父母亲辛苦劳作,虽没能给我们几个孩子大富大贵的生活,却教会了我们自食其力、诚实守信;虽没能买房置地,却培养了一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让孩子们有了自力更生的底气。我们一家人,没有轰轰烈烈,却也在平凡而美好的小日子中不断壮大、蒸蒸日上。